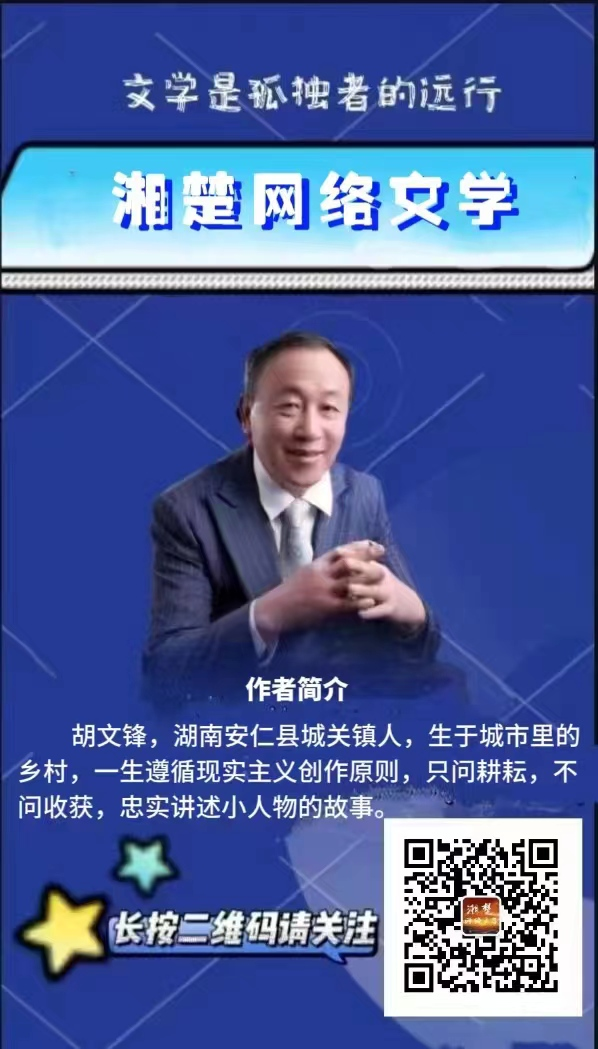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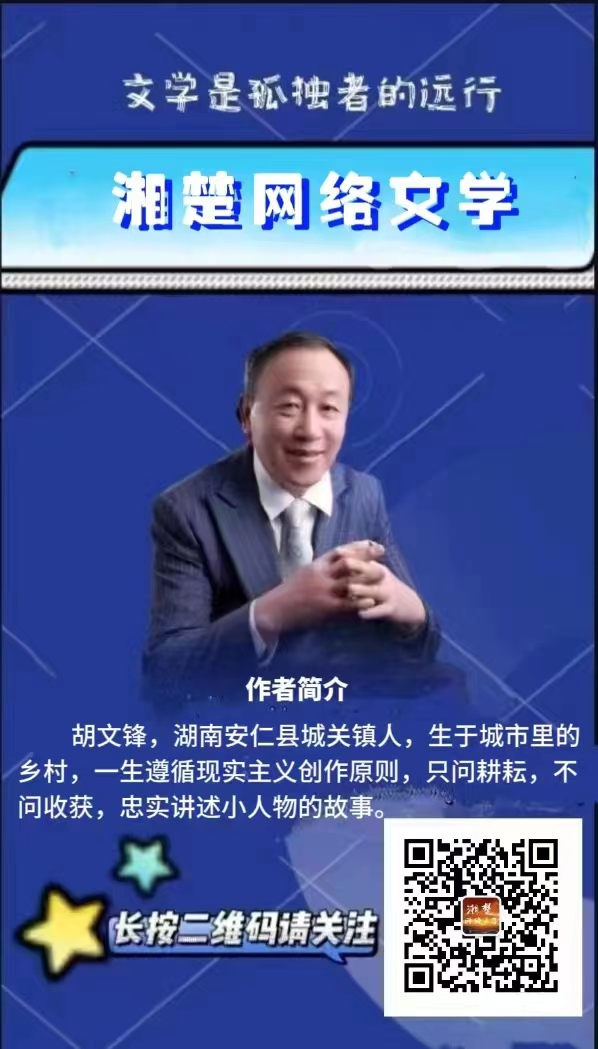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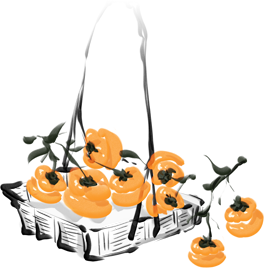
三代人的故事
——前辈的历史,激励刘卓立走过风雨人生路
一、苗竹山
树有根、水有源、人有祖。
能为一个普通人写点文字,我欢喜若狂。我想到本文主人刘卓立老家走一趟,一是了解他先祖的历史,二是感受一下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。
我一提出,马上得到刘卓立、刘庚立、刘炳立三兄弟的积极响应。
刘勰说,“诗人感物,联袂不穷,流连万象之际,沉吟视听之区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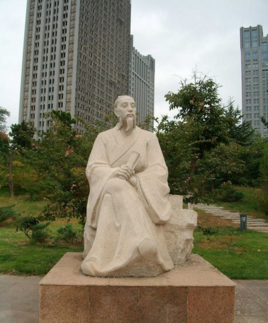
(刘勰)
九月三十日上午,灰蒙蒙的天空好像模糊了我的眼睛,路边的花草,或低头沉吟,或昂首而歌。我爱好沉吟,也热爱歌唱;我喜欢阴天,但不拒绝阳光。阴天褪去了耀眼的光芒后,变得柔和似水,这种水一样的光亮,更贴近人生。人们在其照亮下,演绎着不一样的人生。
当我和刘卓立并驾齐驱,经过一段路程,不远处就是排山芙蓉学校了,他向我介绍说,“1975年,我在队上当出纳,在安仁二中读书时的数学老师谭明珠,带着排山中学谭俊校长找到我,我带他们找到队长刘家信,这块20多亩的烤烟地卖给排山中学,只收了298元。”

(芙蓉学校)
“298元,太少了,农民的土地当时太不值钱了。”我发出一声感叹,他只是怊然若失地笑了笑。
苗竹山位于芙蓉学校后面,不一会儿,我们踏上这片土地,两辆摩托车、两辆电动车停放在组长的禾堂里。
组长贺菊华是一位壮年汉子,我们的不请自来,使他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
“三兄弟,今天何事得空?”
刘卓立指着我说,“请作家来老家看看。”
听到“作家”两字,顿时使我满脸羞涩,脸红到了耳朵根上。喝完茶,我和刘卓立、刘庚立、刘炳立三兄弟结伴而行,一转弯,水泥路两边是一片直插云天的楠竹林。我爱楠竹的超凡脱俗、自善自美的精神,更崇敬它节节拔高、独立清高的气势。

(苗竹山)
刘卓立,是一位74岁的老人了,身高一米六,他长得瘦小机灵,人虽老,却耳聪目明,说起话来像婆娘们叠碗一样,快人快语,一双眼睛放射出精明能干的亮光。
“苗竹山,因漫山遍野的竹子而得名。”他解释着说。他是家中的大哥,又是本文的主角,三人跟着他,在“丁”字路口旁边,挺立着一栋二层楼的钢筋水泥屋,由于几十年没住了,门窗变得斑驳陈旧。这是他“扎根农村干革命”时,于1983年建的,是排山垅里第一栋钢筋水泥屋。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,他认为过上好日子才是老百姓的王道,出完工便私下干点资本主义的勾当,赚点油盐钱。
听了他骄傲地讲述,目睹他神气十足的样子,不得不佩服他是个“精怪”。
俗话说,“一年建屋千年住。”他对我说,“娶孙媳妇时,搬到老家来住。”他对自己手上做的事业总是有着甜蜜美好的记忆。

(刘卓立老屋)
离开老屋,我们继续往前走,四个人登上刘氏祖山牛角坳峰顶,排山垅宝塔坳刘氏的始祖明八公的墓地被青松萃竹掩映着,分外神秘。
明八公,字显亲,明朝御前指挥使,正三品,元至正八年戊子三月十四日生,明宣德四年酉时殁。(公元1346年——公元1429年),屈指一算,至今677岁高龄了。由于辅佐明太祖朱元璋功勋卓著,公元1367年带着弟弟明九公,到明太祖赏赐的安仁熊耳乡(现排山乡)宝塔岭安家立户,繁衍生息。
明八公的后代,散布在排山村宝塔坳苗竹山组、荷树岭组、新湾组、中心组、庙山组、新丰村牌楼组。
明九公的后代,分布在排山村长塘组、芙塘组。
明八公、明九公的后代通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,开花散叶,已成为排山乡的大姓。
我看了明八公保护完好的墓地,对刘氏三兄弟赞道,“明八公的子孙,近700年以来,一代一代年年扫坟祭祖,对始祖的虔诚之心,令人感动。”
一语激起千重浪,三兄弟你一言我一语,叽叽喳喳地讲起了1998年农历10月初一扫祖坟时,在祖山上发生的一件怪异之事。
刘氏子孙为修家谱,给开基公公扫坟,扫祖坟要经过刘自煌的墓地,当时只有一条长满荆棘的羊肠小道。刘自煌墓碑后,一字形长着三棵柏树。秋天,柏树还是那么苍翠,枝叶茂密,尖尖的树顶直指蓝天。

(刘自煌、吴知妹墓地)
路边的一棵柏树妨碍过路,有人举刀要将柏树砍掉,刘声飞拉住他,力劝道,“你要跟主人商量,这样砍不得。”这人说,“没事”。便手起刀落,将柏树砍倒。结果倒地而亡。
对眼前发生的一幕,把刘声飞吓出一身冷汗,他神乎其神地说,“这是一棵神树,砍不得呀!”
难道是冒犯了神灵?否则,这人之死,难以解释。UFO之谜,金字塔的建造之谜等人类十大未解之谜,引起世界顶级科学家成为坚定的有神论者,如爱因斯坦、爱迪生、牛顿、杨振宁……
他们认为“科学的尽头是神学”,恐怕真的有一个凌驾于真理之上的‘神’在主宰人类。
二、外公的逸闻轶事
《安仁县志》第三章第三节卷烟篇记载:“清末,有福建人在安仁开设烟店,推销水烟(烟丝)。”
这个无名无姓的福建人,正是刘卓立的老外公。老外公清末民初从福建省云霄县来到安仁闯世界,他和祖辈一样从事烟草生意,无意之中成了安仁经营烟丝的鼻祖,有了积储后在老正街83号(老地名迎熏路)建起一栋福建会馆。

据城关镇老干部,现年91岁的王宗英回忆,福建会馆和她家隔街相望,刘卓立的老外公娶禾市乡肖古垅女子为妻,生独子吴文聊。
吴文聊首先从军,是个下级军官,退出军界后,当过安仁县警察局长(当时的警察局在老财政局院内)。
王宗英是街上的老妹子,民国1933年,她还是个孩子,对吴文聊记忆犹新。他身高一米八以上,高大威武,手持文明棍,头戴剥秀帽,由轿夫抬着上下班,娶清溪乡周古坪周祥秀为妻,生二女吴玉媛(吴知妹)、吴玉秀(吴细苟)。

(王宗英)
吴文聊无子,当时吴南元流浪在县城,瘦骨伶仃,无依无靠,吴文聊甚是可怜,收其为子。吴南元在新疆某县当过一个月的代理县长。后从军,1949年随董其武将军起义。解放后,以修钢笔为生。“文革”时被打成反革命,他写信给董其武将军,将军反映给邓小平,二十世纪90年代被平反,成了县政协委员。
吴文聊的职业生涯,留下了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的故事。
在一次战役中,作为何健的士兵,在军阀混战中,一连士兵被敌军包了饺子,子弹像煮粥一样咕嘟咕嘟地响,眼见一颗子弹向他的心脏直射而来,他感到大限已到,闭着眼睛等死。在幻灭中,突然见到土地公公骑着一头老虎从天而降,只见他拿着一根拐杖一扫,将子弹轻轻别开。
等吴文聊反应过来时,土地公公骑着一头老虎,腾云驾雾地飞走了。

吴文聊为了感谢救命之恩,朝着土地公公飞去的方向,合掌加额,长跪而拜。
可能是母子连心,妈妈的右眼皮一到晚上就不停地跳,为了保儿子的平安,在城隍庙(防疫站内)跪求城隍爷保佑。
此战结束,只剩下连长和吴文聊两人,战争的血腥残酷,使吴文聊如梦方醒,杀戮战场,不是他走的路。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,子弹是不长眼的,万一阵亡,后果不堪设想,母亲绝不准他回部队,为统治者当炮灰。
从此吴文聊退出军旅,在县里谋了个警察局长的差事。
那时没有检察院,没有法院,侦察、起诉、判决由警察局长一人说了算,吴文聊深深地陷入了苦闷。乱世用重典,他用朱笔勾命之时,右手像触电般哆嗦、浑身颤抖起来。
勾命之后,一个人悄悄来到神隍庙,先在城隍爷面前坐两个时辰,以平息恐惧慌乱的心,再起身跪在城隍爷前,求城隍爷给死者赐福超生。
这种“我不杀伯仁,伯仁因我而死”的难堪,促使他转而敬佛。

(我不杀伯仁,伯仁因我而死)
每年的初一十五吴文聊必到城隍庙给城隍爷烧香拜福,城隍爷是守护一方的保护神,某年的八月初一,窗纸还没露出白色,他去给城隍爷洗澡擦身。走到财神庙(现周石立屋场),突然听到从财神庙传来“抓逃犯”的喊叫声,大声地咆哮声,如鬼哭狼嚎,声声入耳,使人毛骨悚然。吴文聊慌忙冲入财神庙躲藏,一直到天亮。
天亮了,吴文聊怀着恐怖的心理缓慢地走进城隍庙,此时,一条碗口粗的铁锁链甩在大厅中。这是阎王误判逃犯死刑后,“逃犯”不服,将锁链撬开,甩下锁链逃走了……
想到这里,吴文聊跪在城隍爷之前,祈求城隍爷保佑,使“逃犯”逢凶化吉。
这种人不人,鬼不鬼的职业,使他左右为难,最后,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没做完一届,便辞掉警察局长一职,开了一个蜡烛鞭炮小店为生。
讲了吴文聊的故事,请各位看官,跟着我听听民间水师刘华华的故事。
当年,安仁民间著名水师刘华华在吴文聊手下做吹号手,土改时,刘华华在北门珠泉中路(老地名赖霖街)50号分得二间房子(和我家隔壁),以接骨疗伤谋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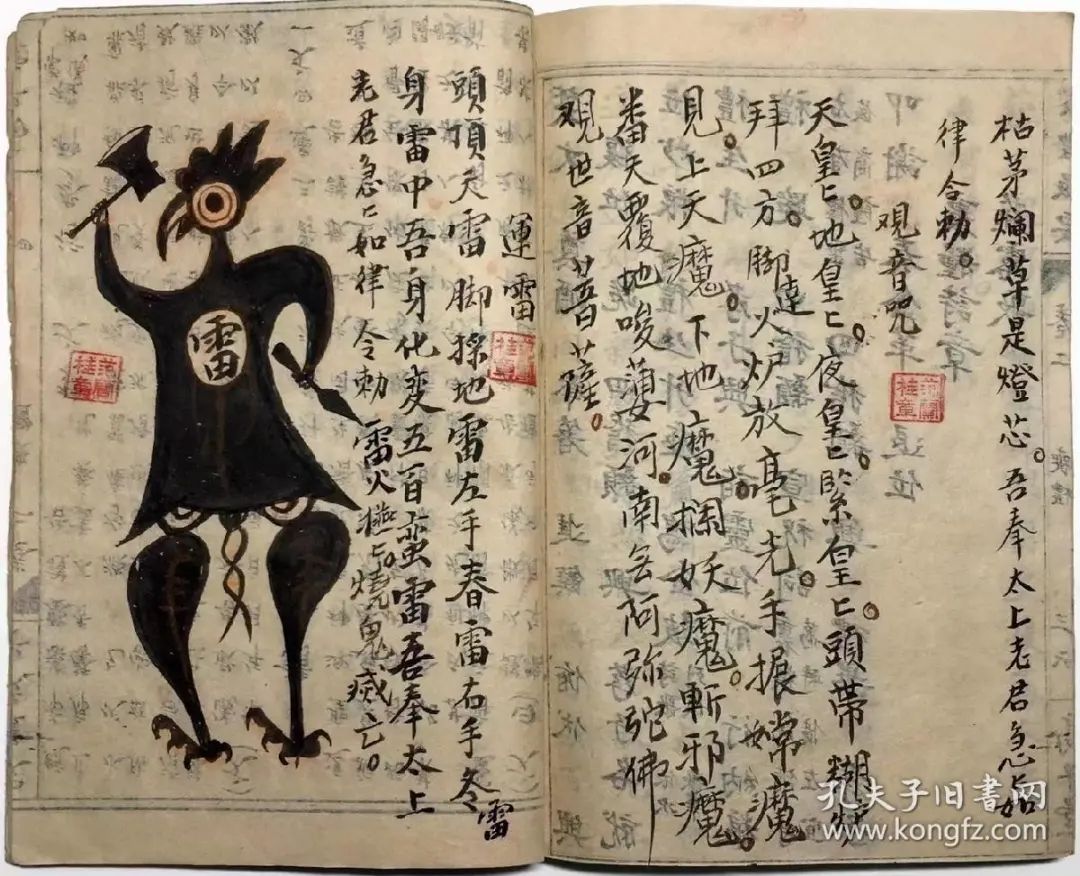
刘华华,洋际乡人,身高一米八,性格温和,待人和善。可说是安仁的名人。他是段邦华婆娘的姨父,1975年去世。
北门街的小孩,遇到跌打损伤,无不得到他的医治。
有一次,我右手骨折,疼痛难忍。刘华华被母亲请来。只见他不慌不忙,装了半碗法水,口中念念有词,用手指对着我右手骨折处写写划划,最后,将口含的“法水”喷射在我伤口处。当时就治住了痛,七天后,右手就活动自如了。
我本想写他的故事,近段时间,到处寻找他的后代,段邦华老师不知道,他的亲女谢冬英也一无所知,仅知道他有个儿子叫黑苟,也不知所终。
然而,在采访刘庭立的时候,突然他讲起刘华华的故事,使我大喜过望。
一天,刘华华穿着青色长袍去绿田赶场,当地一个水师久闻其大名,特意要会会他的功夫,两人互道礼数后,攸县水师并向他暗暗飞出一符,刘华华知道这符来势汹汹,是个索命符。散集后,回到家里,划了一碗水,对婆娘说,“如果这碗水变成凉水,你便给我喝掉;如果不能变成凉水,你就给我买口棺材。”说完便和衣而睡。到了晚上水变成了凉水,婆娘让他喝完凉水,他便坐了起来。
过了几天,他又去赶集。攸县水师,看到刘华华安然无虞,慌忙跑到他跟前,跪下便拜,口称,“师父在上,请受徒儿一拜。”

刘华华二话没说,俯身将他拉起。
(待续)
来源:湘楚网络文学
作者:胡文锋
编辑:段嘉琳
本文为安仁新闻网原创文章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。